
弗里德曼相信,我們正在離開一個以垂直控制與指揮來創造價值的世界,而走入一個與他人聯結、與他人合作來創造價值的世界。人類社會目前正處于這一巨變的前端,一切都在從垂直變得水平。問題在于,世界真的變平了嗎?還是只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人士的一廂情愿?
《紐約時報》的國際事務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2005年推出了他的又一部有關全球化趨勢的專著《世界是平的》,用一種無可質疑的口氣宣稱,“世界是平的”。
世界是平的,意味著在今天這樣一個因信息技術而緊密、方便的互聯世界中,全球市場、勞動力和產品都可以被整個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通過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方式實現。弗里德曼這里所謂的“平坦”,實際意指一種緊密相連的狀態:貿易和政治壁壘的減少、數字化革命的急劇發展,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幾乎可以和地球上億萬人同時做生意,甚至同時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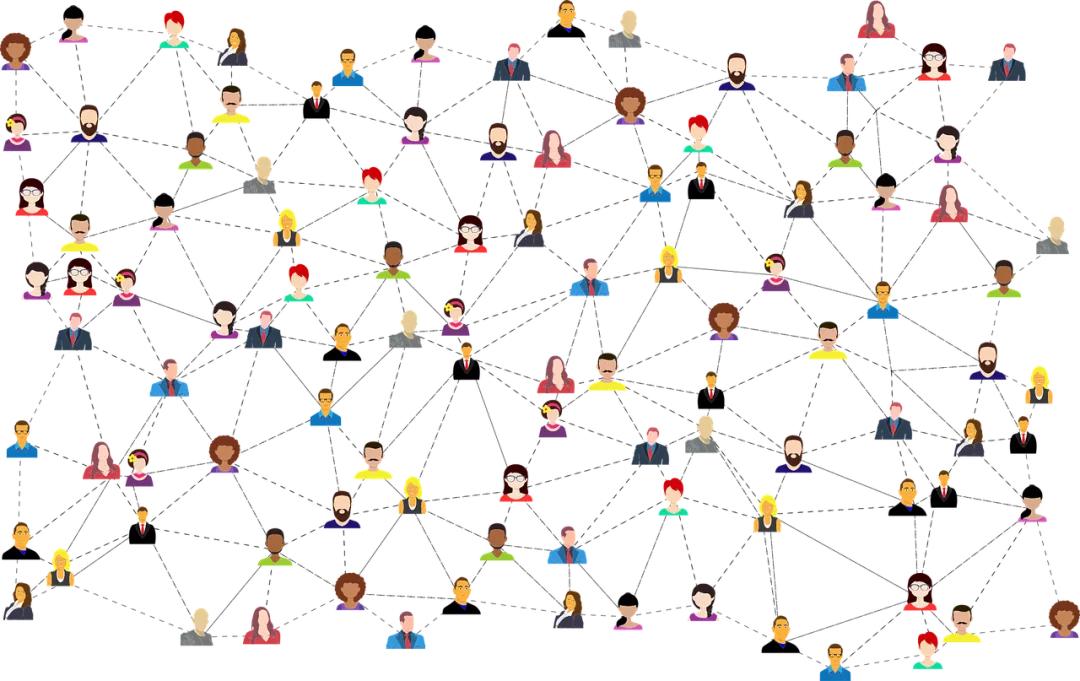

個人的全球化時代:從垂直到水平
在弗里德曼的上一部暢銷書《凌志車和橄欖樹》中,我們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全球化福音書的布道者。在這部新著中,弗里德曼更新了他對全球化的認識,將全球化分為三個階段,并利用網絡術語分別稱之為1.0、2.0和3.0版本的全球化。
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國家的全球化。達·伽瑪(Vasco da Gama)和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代表他們的國家利益探索世界,從而使他們的國家參與全球化,這時1.0版的全球化就開始了,直到最后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結束。這一段時間決定性的因素是國力的強弱,包括武力、馬力、風力和后來的蒸汽動力,它將世界從“大號”縮小到“中號”。
這之后,開始了2.0版的全球化,即公司的全球化,該階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直延續到2000年,它真正目睹了全球化經濟的誕生,跨國公司為了市場和勞力開始進行全球性的議價套利,使世界繼續從“中號”縮小為“小號”(《凌志車和橄欖樹》寫的就是這一階段的情況)。
全球化的最新階段則從2000年開始,3.0版的全球化將世界從“小號”縮為“極小號”,同時夷平了全球的經濟舞臺。但這一時代真正獨特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國家全球化,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個人持續的全球化。
個人必須越來越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將自己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全球化的驅動力是蒸汽船、鐵路、電話、電報和電腦等硬件,那么最新階段全球化的驅動力則是軟件和網絡,它們將全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如果說,前兩個階段的全球化主要由歐美發動,那么最新階段的全球化則向全球各種膚色的人都敞開了大門。

弗里德曼說,在個人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將我們自己“水平化”。我們必須改變自身的工作習慣、學習習慣,必須有創意地修正這些習慣去適應嶄新的平臺。這是因為,我們正在離開一個以垂直控制與指揮來創造價值的世界,而走入一個與他人聯結、與他人合作來創造價值的世界。人類社會目前處于這一巨變的前端,一切都在從垂直變得水平。
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保羅·大衛(Paul A. David)寫了一篇關于電力的文章,給弗里德曼的說法提供了注腳。他問了一個問題:當電力首次出現的時候,為什么人類的生產力沒有突然增加?他研究的結果是,要獲得電力馬達取代蒸汽引擎的生產力提升,人們必須先重新設計建筑,把高大的可以容納蒸汽引擎和各種滑輪的多層建筑物,改成小型的低矮建筑,讓工廠可利用電力馬達運轉。
此后,管理者還要改變他們的管理方法,工人必須要修正他們的生產方式,有難以數計的習慣和結構等待改變。一旦這些改變在某個轉折點產生匯集,轟的一聲,人類就會真正獲得電力所導致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弗里德曼認為,今天我們身處如同電力的改變所顯示的進程一樣,在水平的平臺上,正學習改變自己的習慣,將自己水平化。
弗里德曼說,全球化無可阻擋,美國的工人、財務人員、工程師和程序員現在必須與遠在中國和印度的那些同樣優秀或同樣差勁的勞動力競爭,他們中更有競爭力的將會勝出。
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把全球化當作“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力量,他的這種信念到了不乏偏執的地步,以至于有人嘲諷他患了TIS綜合征(the inevitability syndrome,一般譯為“必然性綜合癥”)。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尖銳地批評說,弗里德曼的策略是“強行把全球化作為人類文明的終極目標灌入人們的大腦,宣揚全球化可以令我們致富,給我們自由,提升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與事”。
企業家、金融分析師和主流政策制訂者無疑會贊賞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論調,然而,來自各界的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在弗里德曼那里好像卻產生不了多少回響。

距離沒有消亡,地理邊界依然無處不在
問題的本質在于,這個世界是否確如弗里德曼所說,是“平”的。
約翰·格雷和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幾年前對全球自由市場的批評今天對弗里德曼依然有效——盡管全球化在所難免,但它并不等同于全球自由市場。弗里德曼未能檢討經濟自由主義令人遺憾的后果——它對教育、健康和環境的負面影響;勞動者收入份額的下降;經濟不平等的令人震驚的發展;不受公眾約束的企業力量的增長,等等。
《世界是平的》一書寫得引人入勝,作者隨處拈來的論據似乎也令人信服,但保羅·克魯格曼的評論一針見血:令人信服的東西不一定是真實的。弗里德曼的主張無疑包含了真相。例如,運輸和通信技術的創新的確壓縮了時空,但是,盡管世界相對而言已經縮小了,這種縮小卻一直并將繼續是高度不平衡的。時空的高度可塑性意味著,有些部分會收縮,而其他部分則會相對擴張。絕非任何地方都能從技術創新中受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世界肯定不是平的。
與“距離的消亡”和“無邊界的世界”等觀察迥異,地理邊界在今天仍然無處不在,甚至延伸到網絡空間。如果說在某個領域中邊界應該變得毫無意義,那就應該是互聯網。然而,國家和地區內的網絡流量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它們之間的流量。就像在現實世界中一樣,互聯網鏈接隨著距離而衰減。世界各地的人們可能會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彼此之間卻沒有聯系。

不僅如此,絕大多數的商業、投資和其他互動都仍然發生在國家內部而不是國家之間。盡管我們到處聽到一個新的連線世界浮現,信息、思想、金錢和人員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快地在地球上移動,但全球化實際上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地方。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即使是這樣很小程度的全球化也很可能會消失。
一言以蔽之:全球化的未來比你所知道的還要脆弱。不如承認這個現實:全球化已經在我們身后。我們應該告別它,并把目光投向新興的多極世界。這一新興世界將至少由三大區域所主導:美國、歐盟和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它們將在經濟政策、自由、安全、技術和社會方面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中型國家將很難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時新的小規模的地區聯盟將可能出現。而20世紀的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將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殺死全球化的有好幾股力量:首先,全球化的副作用日益顯現:財富不平等、跨國公司的統治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分散,這些都已成為熱門的政治問題,使得在政治上反對全球化成為一種時尚。其次,和弗里德曼所認定的技術令世界變平的看法迥異,科技公司似乎正在推動去全球化趨勢,或者它們成為了各國政府實施此類變化的工具。
例如,當多個企業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意識到依賴于復雜全球供應鏈的風險,它們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是從中國向越南或印度尼西亞等其他亞洲經濟體轉移,實現多元化經營;第二種是縮短供應鏈,比如美國公司將生產轉移到墨西哥,歐洲公司則轉移到東歐或土耳其;第三種是發達經濟體投資于機器人和3D打印,以在本地更接近消費者的地方生產。最后這一選擇是技術將會大顯身手的地方。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速度和范圍,使人們感覺自己輕易就可以受到看似遙遠的來自外國的威脅,從而為那些認為關閉邊界是解決各種禍害的方法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結果,新冠病毒危機或許意味著我們將迎來一個全球化程度較低的世界。就算大流行和恐慌癥消退,那些認為對世界各地的人和產品保持開放通常是好事的人,將需要以新穎和有說服力的方式為全球化辯護。
在多極世界中,日益不同的做事方式之間的摩擦、誤解和沖突的可能性很高。從本質上來說,多極化意味著不同的主導區域不會講一種通用語言。人員、思想和資本的流動可能不那么全球化,而是更具區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