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岡這個匠人產業高度化中心,我們一行人和當地的匠人們一起探討了許多有關傳承和創新的話題。
一個只有23萬人口的銅器“大”鎮
在日本本洲中北部,有一個小城市叫高岡,那里是多啦A夢的故鄉,卻藏著一個專屬于匠人的小鎮。
小鎮里的店鋪古樸精致,隨意走進一家小店,和店主攀談幾句,你就會發現,原來他父親的父親的父親就已經在這條街上營業了。簡樸的招牌,淡雅的墻面,這種安靜柔和的生活色調讓筆者感覺仿佛置身于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里一般。

而這個看起來寧靜安逸、與世無爭,只有23萬人口的小鎮,卻出產了日本90%的銅器和漆器。
大概400年前,也就是明萬歷年間,日本加賀藩二代主前田利長在這片土地上筑城,他從《詩經》“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一句中取“高岡”二字為名,還特意請了城外7位手藝精湛的鑄工到城里定居,賜予他們土地,并承諾免除稅金。

于是,高岡的匠人文化之路,就從這兒開始了。
今天的高岡被選為日本重要歷史建筑物群保護區,日本唯一一條被指定為“鑄工街”的珍貴街道也位于此。這個匠人小鎮已經在時光中成長為一個集合創意、技術工廠、線下展示、文創娛樂、旅游生態為一體的綜合文化體了。
千本格子結構的傳統老房子依舊鱗次櫛比,房子里的匠人們拿著父輩傳承下來的錘子,敲打著這個時代的新潮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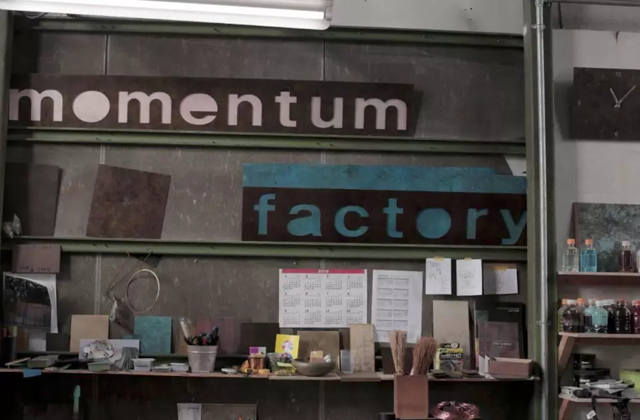
“聽說每年秋天,這邊還會舉辦日本全國手工藝人歡聚一堂的大型活動,這次我們好像錯過了。”中國商業地產研究會會長王永平說,語氣中帶著點惋惜。
是啊,筆者也只能在腦海中幻想,那被橙紅色燈籠戳破的深藍夜幕下,鑄工們穿著工服、合著號子,載歌載舞地在石板路上游行的樣子。
窺探高岡匠人小鎮的運營模式
王永平會長和我們一起參觀了一天的高岡匠人小鎮,作為長期觀察者他對商業地產有著獨到的認識。過程中,他嘴邊時不時地冒出一句“這個好”“這個有意思”;摸著建筑表面時,又自己嘀咕著:“這用的是輕水泥,這樣的工業設計更有感覺。”
看他如此感興趣的樣子,筆者忍不住問了一句:“王會長,你覺得這兒和咱們國內的產業園區,有哪些不同呢?”
“運營模式,運營模式很不一樣。”
在王永平會長看來,高岡匠人小鎮的背后,有著一整套完整的產業鏈模式。國內的產業聚集區內,往往各家各戶都在做相同的產品,互相之間容易形成價格競爭甚至是設計抄襲,產品的同質化競爭最終導致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
而高岡的匠人小鎮里,有人專門做模型,有人專門做著色,有人專門做畫稿,彼此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這其實是一個良性的資源共享模式。

其次,高岡匠人的產品雖然也是帶有新審美的工藝品,但是他們往往都已經經過了4代以上的家族傳承,并且往往是手作的商品居多。
這樣的好處在于讓商品擁有了文化粘性,每一個物件都承載了很強的故事性。同時,因為手作的參與,使得商品價格脫離了單一的成本因素,商品也擁有了更大的附加值。
而相比之下,我們國內新匠人的商品更偏向于文創層面,手作商品的占比相對較小。
性感的產業園區應該什么樣?
“我們目前國內有類似的匠人小鎮嗎?”
“據我所知應該是還沒有……”
“沒有的。”王永平會長話說到一半,他身后的山彪突然出現,作為商業地產資深前輩,山彪對這個問題似乎有很多想說的。
“目前國內產業園區居多,從商業地產的角度看,這些園區的開發商和匠人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租賃和被租賃的關系。”
山彪認為,國內要建設一個真正優秀的產業小鎮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運作,而不是單純以產業園的名義做房地產開發。這個運作是指切實提供傳播、品牌、渠道、社群電商技術、培訓、投資等等方面的系統賦能,這些才是一個產業小鎮的核心競爭力。
同時,山彪還告訴我,在他看來,一個合格的產業小鎮一般需要具備以下5個模塊:一是總部,包括辦公大樓等基礎設施;二是線下展示空間,可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匠人商業街模式,也可能是與使用場景匹配的休閑空間;三是大規模文創工作室;四是生態農業,根據地域情況,與旅游休閑產業做有機結合;五是配套的商業住宅開發。

在問到對本次高岡之行的最大收獲時,山彪說:“他們給自己的服務定位很準確。小鎮內的參觀路線都有統一標識,剛剛帶我們參觀的工作人員其實是這里社長的女兒,但是你看她態度恭敬,語氣謙卑,很低調,但又細心周到。”
這也是筆者的發現,小鎮內地面干凈,街道整潔,基礎設施完善,照顧到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服務人員周到體貼,一切都從客戶出發,圍繞著客戶的需求……每個人都把自己崗位上的工作做到了極致,這些“匠心”同樣值得我們學習。
最后,筆者還從山彪嘴里聽到了一個最新消息:我們已經在著手打造屬于我們的“新匠人小鎮”啦!